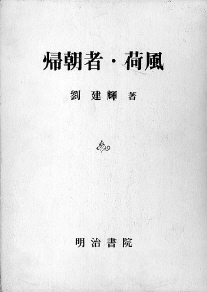

一般说来,近现代史研究在中国的主流是革命与战争的政治史写作,其基本的学术逻辑来自反抗异族压迫的生存经验和历史发展目的论的意识形态信念。但是,如果注意到物质形态的帝国主义力量在中国百余年的历时存在和共时卷入革命与战争的人口及其空间分布的相对比例,如果注意到当今全球化已经进入中国主流知识话语和政治话语而且也被用作阐释世界历史的分析概念,我们就难以忽视探讨中国与世界关系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必要性了;相信这种研究能为我们体会近现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复杂内涵、通过反思文化嬗变的历程促进积极的文化自觉提供最基本的学术支持和理论启示。海外中国学界一向重视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这种传统也培养出了熟悉海外的中国问题资料并能用外语写作的中国青年学者。在日本,专攻中日比较文化的神户大学博士刘建辉先生的日本语新著《魔都上海──日本知识分子的“近代”体验》(日本讲谈社,2000年6月出版),受到了日本学术界、读书界和媒体的关注。
从近代史上看,上海是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异文化接触最具代表性与阐释能力的标本,而西方侵略势力到达东亚以后中日两国不同的应变姿态及其沉沦与崛起的命运则是向历史研究提出的极富挑战性的课题。《魔都上海》正是体现这种学术方向感的著作,它对日本知识分子在西方资本主义进出东亚的“最前线”———上海的体验与感悟作实证分析,揭示了日本现代化启动的国际文化背景,也为人们探讨近代中国的衰败过程提示了社会文化解析的路径。它以日本知识分子对半殖民地中国的认识梳理近代日本人的精神变迁,结果也是中国学者在日本对近代中国的“发现”。
“魔都”上海之命名始于日本大正时代的作家村松梢风,他在1923年春天来上海尽情享受了这个“摩登”都市的放荡和刺激之后,于次年出版了题为《魔都》的上海游历体验记录。他自称被上海的华美、淫荡和放纵这种可以为所欲为的“自由”所吸引,完全沉迷于上海“恶魔般的生活”。显然,半殖民地化的上海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一个既醉心又蔑视的娱乐天国;对于中国人来说,则是没有政治主权和文化主体性而供异族军事统治者、资本扩张者和文化越境者满足欲望的功能化空间。然而,上海的这种“魔性”并不是它固有的,而是西方侵略者所施压迫关系赋予的;也正是在这种关系形成的过程之中,上海对于日本的意义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恰如意为一种竹制渔具的“沪”所表明的,上海在古代是一个渔村。由于其长江入海口的地理位置,南宋咸淳三年设立了检查货物、征收关税的管理机关,元代置上海县;由于这一带较少为战乱殃及,上海并没有其他县所当有的城墙。然而至明代嘉靖年间,倭寇来袭,遂建造了防御城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上海都市文化空间的形成与日本海盗有着直接的关系。
作为棉制品市场的中心和水路码头,上海很快发展成中国繁荣的商业城市;而与日本往来密切的贸易活动,使上海更成为东亚地区的重要港口。清康熙年间,政府采取积极的对外贸易政策,上海便确立了其中国内外贸易中枢和东南沿海大门的地位。鸦片战争失败后,英国领事与上海地方长官协议在上海开辟了作为英商居留地的“租界”,它与以后的美租界、法租界一起,构成了作为“近代都市”上海的原型。不过,在“华洋分居”的原则下,租界虽有一定的自治之权,但仍属中国行政管理。以后,由于小刀会活动和太平天国起义造成难民流入“华洋杂居”的现实以及“安全”威胁,租界逐步扩展界址,设置警察、行政、司法体系,形成了脱离中国行政的“独立国”。于是,上海出现了旧“县城”及其背后的传统水乡与以外滩、南京路等为中心的“租界”所代表的“近代都市”两个对抗、共存的空间。而且,“近代”空间中有着分属英、美、法的租界,这使得上海呈现出多样性的都市景观。另一方面,异文化之间的相互渗透生出一种“混沌”的“世界性”(cosmopolitan);而正是这种“混沌”的变态文化构成了“魔都”上海的“魅力”所在,因为殖民主义权力结构中的“国际都市”有着任何主权国家所没有的“包容力”。
随着半殖民地“近代都市”上海的繁荣和发展,以它为中心,东亚地区的贸易、交通和情报近代化网络形成,并将隔海的日本也卷入其中。当时日本处于江户幕末时期,从上海传来的大量欧美的知识和情报,给维新志士提供了以西方列强为模型的近代国家观念。而且,由于特殊的地缘关系,上海又是日本人踏上赴欧美旅途的“入口”,上海的租界也成为日本人最为近身的“西洋”,许多日本武士或是在前往欧美的途中逗留,或是专程来访,在上海受到了“文明”的冲击。而租界“上海”对县城“上海”的压迫性结构这种半殖民地的悲惨现实,也促使他们下定近代化的决心。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之于日本,是一种“近代国家”的起爆剂。
然而,以明治维新为新的出发点,标榜“文明开化”的日本直接导入欧美的制度,上海便失去了作为获取西洋知识情报的“中继地”的作用。而且,对于推进以民族主义为意识形态基础、建立具有政治凝聚力的“国民国家”的近代化的日本来说,由于上海之“近代”只是沦落为半殖民地租界的象征,它所具有的是与以民族意识想像共同体为前提的国民国家相异的特性,因此是一种危险的“破坏性”存在,它绝不能再成为攀援、学习的楷模,而只能用作在鄙视中玩乐的场所。而上海这种超越近代国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文化空间,处于殖民主义权力结构中而不属于任何特定的国家,在传统规范被破坏以后生出的“现代性混沌”中独具中国“内地”和外国都市都没有的蛊惑人心的“自由”。这样,对于明治以后的日本来说,上海开始转换功能,成为日本人寄托梦想、寻求冒险的乐园和进出大陆的基地。
在明治时代,除了一部分军人和受政府机关、商社的派遣者外,许多怀着“到大陆发展”梦想的日本“脱离者”来到上海。但上海繁华租界和凋敝县城的并存给他们以仰慕和轻蔑的情感体验,不知不觉中就使他们恢复了作为“日本人”的自觉认同,其中不少人成为军部的协力者。进入大正时代,上述“冒险者”族之外又有一群向往“混沌”的上海都市文化的旅行者出现了。其背景之一,是鸦片战争后的上海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由于内外资本的投入和人口的增加而达到其“繁荣”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世界屈指可数的“娱乐空间”。上海作为国际都市,虽然披着繁荣的外衣,但它真正的诱人之处是其“华洋杂居”的“混沌”中产生的“混血文化”(creole)所耀显的“魔性”。和19世纪同样,表现上海作为“魔都”的空间是茶馆、妓馆、烟馆等一连串的娱乐设施。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娼妓的数量也大幅度跃升。到20世纪30年代,360万人口(女性约150万)的上海竟有娼妓约10万,其妓女比例在当时的大城市中是最高的。无论到上海后选择传统的水路欣赏江南美景,还是一头沉溺于上海的情色氛围,日本作家的游记作品里都充满了欲望满足的激动。到昭和时代,摩天大楼群和摩登女郎族的出现以及频发的劳工运动等等给上海的都市空间注入新的“现代性”,其炫丽、过激以及动人的阴暗面仍吸引着日本的一些知识分子,给他们的精神提供了新的滋养。总之,近代半殖民地上海是使日本国家和日本人的存在方式相对化的外部“装置”,正因为有上海这样一个巨大的“他者”,日本才得以早日迎来“近代”,渡海而来的日本人也得以尝试了更加丰富的生存状态。
那么,上海沦落为西方和现代化后起者日本寻求市场、资源和满足放纵欲望的对象地区的社会文化机理是什么呢?从《魔都上海》所作的可称之为列强军事宰制下功能化都市空间形成史的考察,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殖民主义权力结构中的上海由于主权被剥夺的打击而丧失了文化的主体性,无民族意识、非政治意义的求生本能使它变身为刺激外来者欲望的依附性存在,所谓“现代性的混沌”就是这种迷惘、亢奋、自卑性格交织的文化变态的表征。这是著者对国际文化研究的贡献。另外,正如日本评论家所说,著者作为中国人明确自觉到上海之于日本和上海之于中国的两义性,《魔都上海》还为我们提示了思考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上海“入口”。中华民族要争取政治独立和文化主体性,就必须形成凝聚全国政治力量的民族主义意识以重建国家主权。但从中国的社会空间来看,半殖民地化地区虽然是经济的重心,其文化变态的恶性发展使得具有民族意识的政治力量相对弱势化,所以主权重建的巨大可能性只存在于广大的农村地区。中国革命正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思想理论塑造的民族意识从农村找到政治力量载体之后,才逐步走向成功的。但必须注意到,中国革命时期的教条主义和建国后工业化过程中的苏联模式化取向仍暗示着文化主体性缺损的精神负担和后遗症的存留。究其原因,是中国民族主义动员的政治过程中潜在着“欧洲—中国—精英—群众”这样一个等级性话语架构,它妨碍了建立民族国家共同体所需要的民族主义理念的充分发育形成。而且,文化主体性缺损的后遗症一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有效的根除,像把自己的事情想像为“举世瞩目”这种对“被看”的习惯性依赖,像津津乐道“是一个巨大市场”的“肥肉”中国观,像《上海宝贝》对于中国女性情欲和肉体魅力的夸张以及对于西方世界乃至西方男性身体的赤裸裸向往,像西部大开发这种正经的国家发展战略在当地省市竟催生了组赛“西部形象小姐”的选美活动──据称每年一次的选美可以“展示西部独特的风采、情韵和文化魅力”,“形成一条了解、认识、走进西部的视觉走廊”,等等。这种难以控制的自我女性化、情色化、对象化、功能化倾向的下意识流露或积极表现,也许能激发西方的情思与喝采,但也可能如历史曾经的那样招致西方的妄想与蔑视。诸如此类后殖民主义的文化风景,正反映着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染和内化。从世界历史看,文化创造的主体意识决定着民族的地位和未来;所以,如何祛除精神上的殖民状态应该成为我们探索民族复兴之路的重要课题。对此,《魔都上海》有着相当的学术价值──它阐明了近代中国独具特色的的一种文化现象,即原有规范被强力破坏以后发生的“现代性混沌”。这种混沌在民族的心灵世界里是既彻底否定传统中国又难以完全接受现代西方的精神分裂式状态,是一个从思想活动到语言表达都很暧昧、犹疑的空间,其中孕育着种种不易辨别的历史倒退和道德堕落的可能性。因此,应该以严肃的理论和制度创新容纳充分而广泛的探讨,进而凝聚全民族明确而坚定的共识,具有空前历史意义的文化创造主体意识将在这样的过程中生成,相信它是我们真正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应对西方强势文化语境中全球化挑战的精神脊梁。
